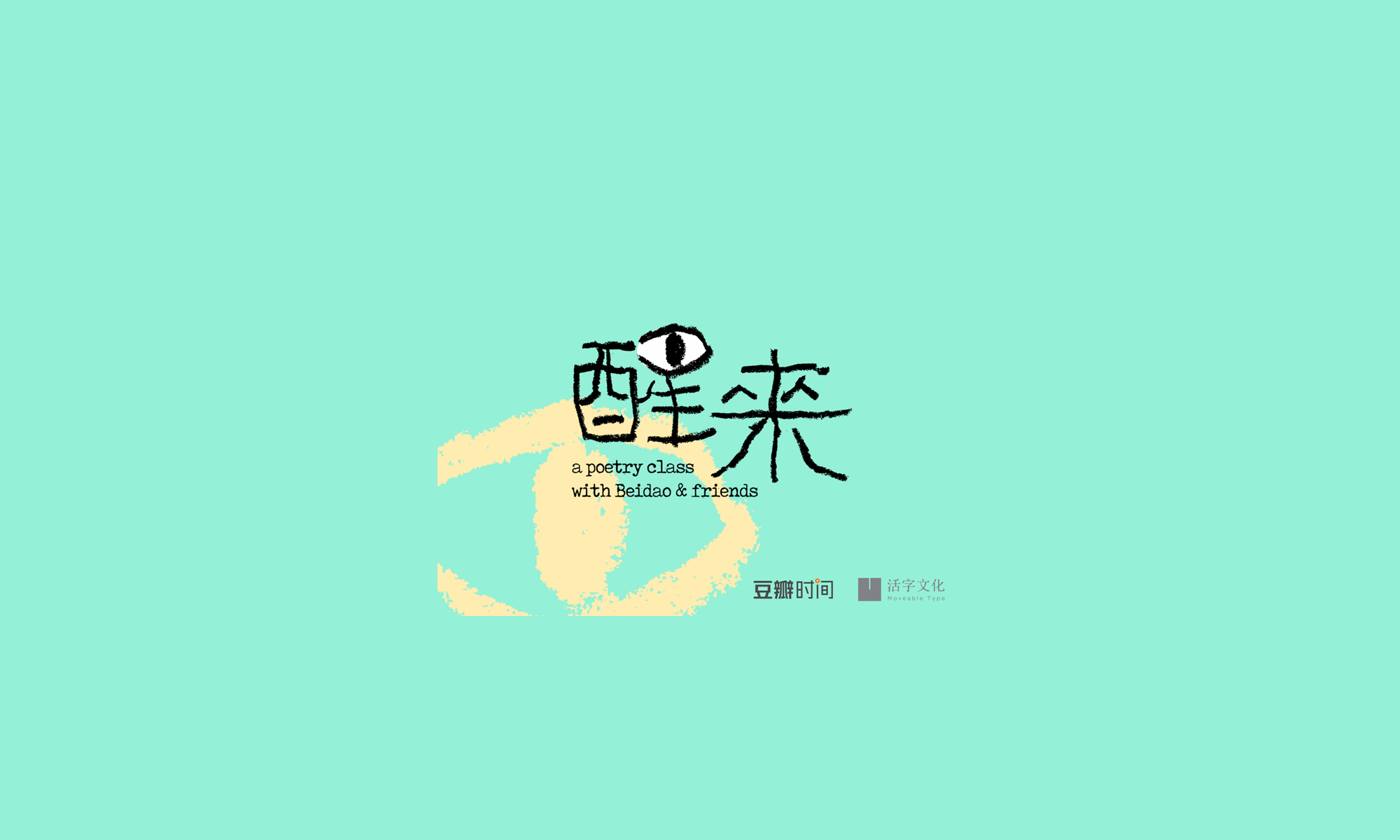近期这个神圣的国度又发生了很多流氓土匪的故事,让人对天朝圣国愈加无语。环视未来,我感到深入骨髓的寒冷与悲望。
无比怀念起李敖,这位和蔼可爱的英雄斗士。
朝阳给我准备了一个“http://李敖.com”,但我很难找回原有的激情,去网络李敖天下的咨询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,都随时有可能被天朝的轮齿碾成齑粉。
我是80后,是中国正值青春的一代人,是所谓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群体中的一名。时代赋予我们伟大使命——成长为社会的中坚。然而,在天朝圣国,一切光彩的设计都如桎梏。其实我更想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表达我的“草泥马之怒”。
我们无法通过努力获得公正的成功,因为这是天朝;我们也无法寄望梦想能够追求,因为这是天朝;我们没有明天,因为这是天朝。
无比怀念李敖,看到他,心中就照耀着阳光。“在这样一个年代,也就李敖值得一见了。”
转子尤的《李敖看我,我看李敖》
给李敖写信当时更真切的想法是“记”,而非“寄”,只是想把一些看法记下来。平时我也有这个习惯,比如当想到一些事会在信上写下“亲爱的”,然后就开始奋笔疾书,也没想是给哪个“亲爱的”。再说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寄呢。
后来有幸由朋友转交,并没有回音,我也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继续自己的生活,因为治病养病是更重要的,而李敖的书在我病房里那浩如烟海的书堆中只是很少一部分。就像我跟记者解释的那样,如果张爱玲活着我也会给她写信,但我转念一想,张爱玲性情古怪,估计不会给我回信,而李敖与她不一样。
李敖对于我一点儿不陌生,他一口的北京话,而那些台湾人,反而显得与他有天生的区别和隔阂。李敖小时候住在内务部街,在新鲜胡同上小学。而我妈妈小时候就住在那一带,我妈妈和大姨都是在内务部街上的学,分别是七十二中和二中。所以李敖不是高高在上的,不是端着架子的,而像一个胡同里的老爷爷,近在咫尺,从我身边走过,两个人问好,微笑。
我在信里谈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,因为他就很不适应学校生活,曾在回忆录里写道:“读的课外书愈多,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。”还说:“时光倒流,宁愿少活十年,也不要从过中学生、大学生那段日子。”
李敖是个很独立的人,且有傲骨,他就是觉得自己学比在学校学收获更大,而他认为教育是冷冻机的看法也与我惊人吻合,我自然要与他聊聊,这种聊毫无顾忌,谈天说地,无所不涉,不是追星fans的抬头仰望,而是一老一少,平起平坐的“旅行”。
很多关于李敖来看我的报道,都会把我写成不折不扣的“李敖迷”,或者将我们描写成”老少狂人”。其实我三月份就开始写信,只为记下心得,李敖要来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,当时我还以为他此生都不出台湾了呢,难道要我把他从台湾叫回来?而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不崇拜李敖,反而显得我更狂了。其实我想,不选择“抬头仰望”的方式与他交流,就是因为当人有了足够的思想高度时,就不会轻易被左右,而能够冷静面对一切,自然也就不会有崇拜之想。而我也不会在信中请求他来,李敖也不是被呼来唤去的主。每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时,都会称其为“李敖大师”,但我自始至终没说过大师二字,给他题字时也只是写“李敖爷爷”,使得他对此“不满”。
在台湾媒体来采访时,我是这样说的:“我就像李敖爷爷一样,不随便崇拜人,我只是欣赏他,将他的人生铺展开来,让我知道,人也可以这样活着,他做了我们所不能做,说了我们所不敢说,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和痛快的。其实李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,就是他自己。”
9月21日上午,我在看凤凰卫视直播李敖在北大的演讲,不时的有电话和来人。临近中午,凤凰卫视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拍病房环境。我当时面目僵硬,穿着漂亮衣服,说不紧张不可能,应该说当时我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自己紧张了,属于脸不变色心乱跳。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太不一般了,李敖12点来,而我是给自己逐渐施加着压力。妈妈到阳台往下看,简直就是人满为患、人声鼎沸、人山人海……反正就是人多得不得了,当然记者居多,他们都被拦在了警戒线外。突然,我听见楼下传来喧闹声,然后有人说:“来了来了!”因为我无法用眼睛追寻过程,只能用耳朵来想像,只听得楼道里脚步声密密麻麻,如钱塘江大潮般袭来,霎时间我有种要被淹没的感觉,没有紧张激动,只有默默接受,脑海只闪现两个字:来了。
我靠在床上望着门口,等待李敖的出现。然后,李敖就出现了,仍是穿着刚才在北大演讲时穿的深色西服、白裤子,打着一条红领带。因为每天都看《李敖有话说》,看着他做动作、说话,当他在我面前展现我所熟悉的这一切时,我觉得好有意思,他就像从电视里跑到我眼前。
李敖非常谨慎,说不跟我握手了,走到床边,墨镜后的小眼睛审视着我,如变魔术般拿出一本小书,正是我在信中提到想找的《教育与脸谱》,这是1964年版文星丛刊之75,他笑着说:“我带来了你没有的东西,我留着不写字,到这儿再写。”又说:“我没想到你这么高。”说话间坐到了椅子上,拿出自己心爱的钢笔,似乎铆足了劲要证明自己的“一级棒”字。他说:“我用你们的话来写”,在扉页上写道:目有余子尤其是你。写完就说:“先给妈妈过目。”
而我也不落后,将自己的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拿出,上面有我刚刚整齐写过的字,我笑着跟他说:“字没你好。”说完便大声念道:“你也曾青春似我,我也会快意如你;谁敢喊虽千万人吾往矣,谁又将两亿年握在手里。9月21日(构思于9月19日下午,其时你在天上)。”李敖听罢,说了声“好!”两人心有灵犀,不言自明。
自始至终,李敖都与我保持距离,尊重着我的病人身份,我不禁想起几十年前,青年李敖初次见胡适时对他的描写:礼貌周到,亲切可人。现在我要说,李敖也配得上这八个字,其老辈风范一展无遗,很是感人。我给李敖展示自己的伤口,他又笑着说起自己的病。我想到17岁的李敖看到钱穆时的情景,他觉得钱穆个子很小,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,简直使李敖有点怀疑眼前这位,是不是就真是钱穆。时光流转,眼前坐着的李敖爷爷就不怕我看他,心里也对他有不好的印象吗?哈哈。
我要送李敖到楼下,李敖坚持不让。我坐在轮椅上,同李敖一起坐进电梯下到一楼,电梯中我抓紧时间问他:“你对死亡恐惧吗?”李敖说:“原来有,现在不了。”没等他说完这话,电梯就到一楼了,我被推到医院门口,然后就看见了在电影里才会看见的场面,门前小小的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,对面的门诊楼的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探出来的头。闪光灯几乎比那天毒辣的阳光都要强烈,我要求从轮椅上站起来,与他并肩站着,因为我这样挺拔的身材,坐在轮椅上照相岂不是可惜!不就更印证了“探望病童”的概念?于是我站起来,和李敖并肩站着。我转头看着他,看着一张七十岁的脸,想从中找寻出什么。他在书中写了那么多自己的信念,理想,但那毕竟是文字。而我眼前站着的,是一个真实的人,活生生的人,七十岁依然在战斗着的人。我曾经感动于他那句“不管别人怎样看我,我都不介意、不沮丧”,他说过:“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。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,可是我走了。”如今,我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,也终将要行进起来,走上前去……
我抓紧时间又问他:“你想过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?”这个问题也源于我病床上的思考,比如说李敖,他来到这世界上,奋斗了七十年,时光匆匆流过,他满意吗?来到这世上只为了这曲折奋斗的七十年吗?
他笑着回答:“这要问我爸爸妈妈。”接着就被工作人员带着下了台阶,上了车,当时的情境太紧张,太快了,也不是个说话的场合,不过我对这两次简短的谈话还是很满意的。
突然想起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:“在这样一个年代,也就李敖值得一见了。”